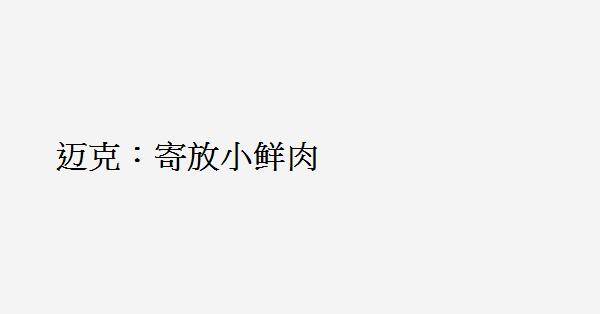
《午夜巴黎》那麼交游廣闊,塞納河左右逢源,仍然不忘快閃Rue Malebranche,可見這截短短的小巷真是人見人愛。半邊路微微傾斜,半邊路可由八九級石階拾級而上,結構有點像香港跑馬地鳳輝台,不過當然更古雅更清幽 ——沒有外景隊金鼓齊鳴進行二次創作的時候。導演們特別鐘情的,應該是路面鋪石子,俗語說「一白遮三丑」,石子路營造的氣氛也有類似效應,水銀燈一打在上面,要多晶瑩有多晶瑩要多陰森有多陰森。據說從前這區全是石子路,1968年5月學生運動時,因為手無寸鐵的莘莘學子就地取材,挖出石塊充當抗爭武器,風潮過后政府重建,大部分改鋪柏油以絕后患,由治而興,犧牲了濃濃的中古世紀色彩。
街頭由好萊塢玉女鼻祖柯德莉夏萍坐鎮,街尾有家殘舊的小旅館,曾經棲宿貝托魯奇(Bernardo Bertolucci)《戲夢巴黎》(The Dreamers)那名闖進高克多式家族游戲的美國小青年。2003年貝先生選中它寄放小鮮肉,旅館仍然營業,大約十年前經過,發現不知道幾時已經悄悄結業了。疫情期間,有個藝術細胞發達的流浪漢在門洞搭了一張床,毛毯被單重重疊疊,其心思獨具,簡直令人想起張愛玲《童言無忌》寫的「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以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。
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,而是參差的對照,譬如說,寶藍配蘋果綠,松花色配大紅,蔥綠配桃紅。我們已經忘記了以前所知道的」。
貝托魯奇將探戈跳上普羅觀眾的[色.情]禁地前拍過一出《同流者》(The Conformist),也在巴黎取景,其中一場鏡頭擺在奧賽美術館外。如今游客如梭的觀光勝地,60年代末70年代初猶如廢墟,原本的火車站再沒有汽笛聲,附設的豪華大酒店也關門大吉,《同流者》為了重塑兩戰間花都的紙醉金迷,故意讓度蜜月的新婚夫婦在它門前耍花槍,考證的認真當然不亞于王家衛的《繁花》。
嚴禁無授權轉載,違者將面臨法律追究。
文章未完,點擊下一頁繼續
下一頁


















